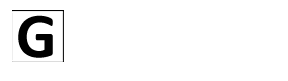威廉 福克纳(威廉福克纳作品)
新课标语文课题组:黄雅丽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第一高级教师,河南省骨干教师
主编:王涛
栏目主编:杨文慧 / 责编:左佐
审校:张婷 / 美编:马云
【编者寄语】
福克纳笔下的这位父亲穿着“硬邦邦的黑外套”,有着“金属丝般坚硬的身躯”给人一种阴暗、冷酷的感觉;因为受伤跛着脚,让他显得怪异无比,种种生活的重压让他的心中燃着一团火,所以他习惯用烧马棚的方式解决一切与邻居或雇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暴戾、极端的处事方式让全家人跟着他颠沛流离,当父亲又一次与外界的矛盾激化时,十岁的小儿子沙多里斯在面临正义公平、家庭观念、血缘关系等处世规则时, 内心是如何冲突、做出了怎样的艰难抉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对别样的父与子吧!
【文本研读】
烧马棚
威廉·福克纳
①“你可得放明白点儿,地毯已经叫你给弄坏了。这张地毯值一百块钱,可是你自出娘胎还不曾有过一百块钱,所以我要在你的收成里扣二十蒲式耳①玉米作为赔偿。下次再到公馆里去,可要把你的脚擦干净点儿。”
>>>小说一开头就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吸引读者的兴趣。悬念一。
②说完骑马的人就走了。孩子看了看爸爸,爸爸一言不发,连头也没有再抬一下。
③那是星期三的事。从这天起孩子就一个劲儿地干活,不停地干到周末;干得了的活儿他干,有些干不了的活儿他也一样干,不用逼着他,也不用催促他,他干得就是这样勤奋。他心里想:说不定这一下倒可以彻底解决了。为了这么一张地毯赔上二十蒲式耳,虽然好像有点难受,可是只要父亲能从此改掉那个老脾气,再也不像从前似的,花上二十蒲式耳说不定还划得来呢。想着想着,不觉想入非非了:也许到时候一算账,都抵了个精光,那就完了——什么玉米,什么地毯,干脆来一把火!可怕啊!痛苦啊!简直像被两辆四挂大车两边绑住,两头一齐往外拉!——没指望了!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①-③,为故事的开端。采用倒叙的手法,叙述孩子为爸爸弄脏了雇主家的地毯而苦恼。
④转眼到了星期六。孩子跟爸爸乘着大车进了作为法庭的杂货店,看见木板桌后面坐着的那个戴眼镜的人,不说他也知道那是位治安官,他向治安官大声嚷道:“他没干呀!他没烧呀……”
⑤“快回大车上去。”爸爸说。
⑥“烧?”治安官说,“你是说这张地毯已经烧啦?”
⑦“谁说烧来着?”爸爸说,“快回大车上去。”可是孩子没有去,他只是退到了店堂的后边,听着堂上的问答。
⑧“那么你是认为要你拿二十蒲式耳玉米赔偿地毯的损失,数目太大了点?”
⑨“他把地毯拿来给我,要我把上面的脚印洗掉。我就把脚印洗掉了,给他送了回去。”
⑩“可是你给他送回去的地毯已经不是你踩上脚印以前的那个原样了。”
>>>这段对话言简意赅又信息量极大。爸爸阿伯纳是一位南方白人佃农,由于在战争中偷了马匹逃跑时,被子弹射中而成为终身残疾。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无法接受的生理缺陷导致他心理的严重扭曲。使得他对周围所有事物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对战争和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人和事产生深刻仇恨。当他来到白人地主德·斯班少校家时,他开始意识到,白人地主是不会对穷人心存怜惜的。他模糊地知道地主家的财富和体面生活全是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换来,从前是剥削黑人奴隶,可是战后蓄奴是违法的,就转而剥削自己这些穷白人。所以他压制不了内心的怒火和不平,故意脚踩马粪,弄脏雇主家的地毯,清洗时又弄坏了地毯。
?爸爸一言不发,室里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响动,持续了足有半分钟之久。
?“你拒绝回答吗,斯诺普斯先生?”爸爸还是一声不吭。“我就判你败诉了,斯诺普斯先生。我裁定,到收获季节你应该在契约规定以外,另从收成中提出十蒲式耳玉米缴付给德·斯班少校作为赔偿。退堂!”
>>>④-?段为故事的发展。法官裁断爸爸给德·斯班少校赔偿。
?直到太阳下山以后,他们才到了家。在灯光下吃过了晚饭,孩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夜幕终于完全罩上了。他正在听夜鹰的啼叫和那一片蛙鼓,忽然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干不得!干不得!哎呀,天哪!天哪!”
?正在这时,爸爸看见孩子站在门口。
?“到马棚里去把大车加油用的那罐油拿来。”爸爸说。孩子没动,半晌才开得出口来。
?“你……你要干什么……?”他嚷了起来。
?“去把那罐油拿来。”爸爸说,“去!不要让我揍你!”
?敢情那老脾气又来了,那古老的血液又涌上来了,孩子心里想着,终于挪动了腿,一到屋外就拔脚向马棚里奔去。我要是能一个劲儿往前跑就好了。我真巴不得能往前跑啊,跑啊,再也不要回头,再也不用去看他的脸。可是不行啊!不行啊!他提着生了锈的油罐奔回家去,罐里的油一路泼剌剌直响。一到屋里,就听见了里屋妈妈的哭声。他把油罐交给了爸爸,但他多么希望爸爸改变主意呀!
?爸爸说了声:“揪住他!”妈妈抓住了孩子的手腕。“不行,要抓得牢一点。要是让他跑了,你知道他要去干啥?他要上那边去!”说着把脑袋朝大路那头一摆。
?爸爸走后,孩子就挣扎了起来。妈妈两条胳膊把他紧紧抱住,他把妈妈的胳膊又是撞,又是扭。突然他挣脱了。抓他也来不及了。他一路奔去,气急心慌地顺着车道向那亮着灯光的大宅子奔去,他连门也不敲,就一头闯了进去,抽抽搭搭地喘不过气来,半晌开不出口。
?他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找……”话没说完,他看见少校从穿堂那头的一扇白门里出来了。他就大叫:“马棚!马棚!”
?“什么?”那白人说,“马棚?”
?“对!”孩子叫道,“马棚!”
?他听见少校在他背后喊叫:“备马!快给我备马!”
>>>沙多里斯在对家庭的忠诚和他自己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感受的冲突中被割裂了。虽然之前他选择作伪证帮助爸爸,但这次爸爸烧少校的马棚时,当沙多里斯的忠诚再次遭到考验时,他果断地跑到得斯潘少校家通风报信,可见孩子身上“善良,正义”好的一面本性战胜了血统和家族中“邪恶,暴力”的一面。
?可是就在那人影马影尚未消失的当口,夜空里像是突然狠狠地泼上了一摊墨污,不断向上扩大——那是冲天而起的一团团浓烟,惊心动魄,却又阒寂无声,把天上的星星都抹掉了。孩子撒腿奔去,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可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奔,听见了枪响也还是往前奔,一会儿又是两声枪响,他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叫了两声:“爸爸!爸爸!”又不知不觉地奔了起来。他跌跌撞撞的,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赶紧又连跑带爬地从地上起来。起来后匆匆回头望了下背后的火光,就又在看不见的树木中间只管奔去,一路气喘吁吁、抽抽噎噎地喊着:“爸爸呀!爸爸呀!”
>>>?-?段为小说的高潮。孩子向少校揭发了爸爸烧马棚的行为。
?午夜时分,孩子坐在一座小山顶上。天上渐渐星移斗转。天就要亮了,再过些时候太阳也要出来了,他也觉得肚子饿了。他就站起身来。他觉得身子有点儿发僵,不过走走也就会好的,正像走走就可以不冷一样。何况太阳也就要出来了。他就向山下走去,向那一片黑沉沉的树林子里走去,从树林子里传来一声声清脆的银铃般的夜鹰的啼叫——暮春之夜的这颗响亮的迫切的心,正在那里急促地紧张地搏动。他连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了。
>>>?段为小说的结局。孩子离家出走了。
①蒲式耳:计量单位,1蒲式耳约合35升。
《烧马棚》是一部关于南方内战后的南方家庭小说。畸形的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促使了家庭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矛盾激化、加速并推进了旧南方分崩离析的步伐。福克纳在小说中展现家庭故事、家庭关系的同时,也表现了南方家庭的腐朽和败落。福克纳正是在小说中通过描绘这些暴君式的家长残忍的和非人道的行为来揭示旧南方的解体和旧秩序的失败。
【知识建构】
//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事世界的时候,他必须创造性的运用叙事谋略,其中叙事视角就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把作者全知的圆切割成文本中限知的扇面,也就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的钥匙。福克纳的作品有非常复杂的叙事视角切换意识,《烧马棚》就是其中代表之作。
节选部分开始是一段骑马人的话,采用第一、第二人称交叉,第二段转为第三人称。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叙述者的显著特征是:福克纳巧妙地使用了“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并通过两类视角的转换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小说的整体部分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为主。“零聚焦”对应“第三人称”,即全知视角。用热奈特的公式就是叙述者大于人物,也就是说叙述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他全知全觉,而且可以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创如何知道的,没有聚焦任何人,但又全知全能。本文节选部分就以第三人称即全知视角为主,自由灵活,多角度多侧面展示相关内容。我们随着孩子的所见、所感、所闻经历体验了他偏执的父亲和治安官交锋、以及当父亲又要烧德·斯班少校家的马棚时他面临选择正义还是忠诚时的矛盾等一系列事件。这种视角的选择在突出父亲虽坚定、不屈不挠却又暴戾、偏执、自私的性格方面更有说服力,如“到马棚里去把大车加油用的那罐油拿来。”爸爸说。孩子没动,半晌才开得出口来。而且不断的心理描写则让读者近距离的体验到了孩子的矛盾与挣扎,小说对孩子的心理描写给人真实可信感。如“他提着生了锈的油罐奔回家去,罐里的油一路泼剌剌直响。一到屋里,就听见了里屋妈妈的哭声。他把油罐交给了爸爸,但他多么希望爸爸改变主意呀!”全篇小说没有出现一个“矛盾”“挣扎”这些词,然而通过心理描写,却能让读者近距离地体验到孩子对父亲复杂矛盾的心情。
这种叙述视角最大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视野无限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因此颇受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其次是便于全方位地描述人物和事件,如文本最后一段的场景描写。另外,可以在局部灵活地暂时改变、转移观察或叙述角度,这既多少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又使叙事形态显出变化并从而强化其表现力。叙事朴素明晰,读者看起来觉得轻松,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但是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形式并不是最完美的。为了免于读者被动地“听”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而能积极地参与到叙述世界中去,在叙述中间,作者对叙述者形式进行不断的切换。如在堂上的一段对话“‘那么你是认为要你拿二十蒲式耳玉米赔偿地毯的损失,数目太大了点?’‘他把地毯拿来给我,要我把上面的脚印洗掉。我就把脚印洗掉了,给他送了回去。’‘可是你给他送回去的地毯已经不是你踩上脚印以前的那个原样了。’”作者精心地设计了这里叙述者形式的转换,作者努力将叙述者形式由全知全能式转换到有所限制的第一、第二人称叙述者形式,而且这种转换在文中下面的第?????自然段不间断出现,交叉使用。尤其是第?自然段“我真巴不得能往前跑啊,跑啊,再也不要回头,再也不用去看他的脸。可是不行啊!不行啊!他提着生了锈的油罐奔回家去,罐里的油一路泼剌剌直响。一到屋里,就听见了里屋妈妈的哭声。”这里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来描摹孩子的心理,对孩子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内心观察,这些心理描写自然而又真切地传达了孩子渴望安定平静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临选择“血缘”还是道义时的矛盾。全文以对话体这种形式自由地变换叙述者形式而又令读者难以觉察。两种叙述视角,多种叙述者形式既相分离又相统一,这种独特的叙事角度对于作者加强叙事能力、突出叙述者的功能以及增强叙述魅力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Tags:
相关推荐
-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60925996.99 元中标红林总装厂房二期工程
- 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龙里县城区排涝工程勘测
- 北京中和联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标山地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植物表型研究设备采购及伴随服务(重新招标)项目,中标金额 7764000 元
- 霸州市佳理鑫五金制品厂中标新乐市第三中学采购项目
- 河北泽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等为路南区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一期)一标段工程总承包(EPC)(二次)中标候选人
- 河北石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110736.93元中标高铁片区景观提升项目施工三标段
- 中基恒源建设有限公司中标高铁片区(含新华商业广场)景观提升项目施工五标段,中标价 13430852.95 元
- 九芝堂换帅完成工商变更
-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宁县水果供应链基地运营配套建设项目施工(二次)第一中标候选人
- 浙江宁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97028327元中标慈溪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转运一体化建设项目(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