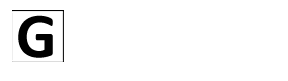诗谱序全文(诗谱序原文翻译)
完成于汉儒之手的《诗大序》,是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继承与发展,并对嗣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传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四家。后来今文三家诗亡佚,只有用先秦文字小篆记录的《毛诗》独传。在东汉流传的《毛诗》,于305篇的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要文字,简述诗的题旨,或述及时代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其中第一篇《关雎》的题解下面,有一大段文字,广泛吸取了先秦学者及汉代经师对《诗经》的评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特征、《诗经》的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可以看作是《诗经》的总序言,称作“大序”。其余的题解都称作“小序”。“小序”所作的各诗的题旨、作者或时代背景,大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穿凿附会,有许多内容存在着严重的谬误。由此可以确定“大序”、“小序”非一时一人之作。有学者认为“大序”反映了荀子学派的观点,而“小序”则出于孟子学派之手,故较多体现了“以意逆志”的方法。
《诗大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论诗的基本特征:
《诗大序》一开始就阐述了诗歌的性质及产生情况: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诗大序》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诗言志”说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于“志”字之外,加上了一个“情”字,指出诗、乐、舞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是对先秦诗论的重大发展。
本来,“志”的本义是与“情”相通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唐孔颖达《正义》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志”长期被儒家学者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则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并因此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和争辩。而事实上,如果按照儒家学者的解释,把“志”统统看成与政教相关的思想,那么在诗歌中确实存在的一类既非讽颂、也没有什么教化作用,因而称不上是“言志”的作品,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所以,诗歌发展的实际,要求理论给予圆满的解答。《诗大序》正是在人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深入的基础上,将“情”、“志”并举,于“言志”之外,加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这一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诗大序》在情、志并举之后,进一步把二者统一起来: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要把感情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也就是照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诗大序》用“礼义”把抒情与言志统一起来,建立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歌理论。
二、论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
《诗大序》的中心内容,是提倡诗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通过诗、 乐的感化作用,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它说: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不难看出,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说和“事父”、“事君”说的继续和具体化。但《诗大序》对此有继承也有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阐明了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即“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上以风化下”,就是要求统治者利用诗歌作为推行教化的工具,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道德规范对臣民进行教育。“下以风刺上”,则允许在下的臣民当对政治和社会现实不满的时候,可以用诗歌为讽刺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不过对于“刺”,《诗大序》又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主文而谲谏”,即必须用委婉的言词含蓄地进行劝谏,不可直言统治者的过失,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二是要求统治者实行“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政策,容纳和鼓励以讽刺为内容的诗歌。这里固然表现出《诗大序》的作者们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要求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伪善、保守的一面。但也毕竟给被统治者利用诗歌反抗和抵制统治者的暴政,提供了一点哪怕是很微弱的理论支持。后世进步文学家往往正是以这一理论主张为根据,巧借文学武器同封建阶级的不良政治进行斗争,这可以看作是《诗大序》讽刺理论的积极意义。
诗歌通过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进而反映人的社会生活,而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生活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通过诗歌可以考见政治得失,这就是孔子所谓“诗可以观”。《礼记·乐记》把这个意思概括为“审乐以知政”。《诗大序》采取《乐记》的见解,写道: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里说明诗歌、音乐都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诗乐反映着各个时代的面貌,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乐。强调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诗歌理论的一大特色。它同时也提醒人们意识到,政治的兴衰隆污往往要通过文学艺术显出其征兆。因此,审察评判文坛风气,切不可就事论事,要联系和反省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文风的端正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世风民情的端正。从改良社会、革新政治入手,标本兼治,才能创造出安定祥和的“治世之音”。
三、论诗的“六义”:
《诗大序》提出“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人往往以“风、雅、颂”为诗的体裁;“赋、比、兴”为诗的表现方法。这种说法来自唐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考“六义”说实本于《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过去一般认为“六诗”原都是指诗之体,但有入乐与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把不入乐的“赋、比、兴”诗给删掉了。待《毛诗序》的作者论诗时,面对的只有“风、雅、颂”三体,但又不能不维持“六诗”的旧说,保持其原来的次序。于是回护其辞,而改称“六义”。“赋、比、兴”也就逐渐被后人理解为诗的表现方法了。近年有学者认为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的史诗唱诵和乐舞。其中“风”和“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和“兴”是用歌唱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歌与和歌;“雅”和“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与舞歌。今本《诗经》的各种格式均是六诗影响的产物。从六诗到六义的演变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因素有三项:一是随著神权政治削弱、雅言功能扩大和礼乐制度崩坏,由司乐之官掌管的乐教逐步让位于由司徒之官掌管的德教;二是诗三百文本的形成,其过程大致是散乐纳入正乐、乡乐奏入仪式、献进之诗编为正歌的过程;三是儒家诗学传统的确立,包括孔子集各地歌本删为诗三百、孟子建立“以意逆志”的比附诗论、荀子确立徵圣宗经原则等步骤。作为汉代经学的组成部分,六义说是演绎“德化”、“政教”、“美刺”等儒家伦理概念的理论,但因保存了六诗、“四始”、“变风”、“变雅”等若干历史术语而具有价值。①此说颇有见地,故辑录如上以备参考。
总而言之,古代原有的“六诗”传到儒生们写《诗序》的时代,只剩下了“风雅颂”三体。于是《诗大序》不得不改传统的“六诗”说为“六义”。“诗六义”说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六义”名称的解释。《诗大序》指出“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即风是产生于各国地方的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它说“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祭祀、赞美祖先的乐歌。这种对于风、雅、颂三类诗歌区别的理解,比较合乎事实,直到今天仍是解说《诗经》分类的重要依据。但《诗大序》的解释也有过于强调教化意义之嫌,容易导致从政教观点出发对诗篇内容的曲解。
此外,尽管《诗经》中已无“赋、比、兴”三类诗的存在,但《诗大序》仍保存了先秦的“赋、比、兴”概念,并把它们作为诗“六义”的组成部分重新提出。虽然它对“赋、比、兴”的涵义没作具体说明,但引发了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之成为对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中国式的理论概括。这也是《诗大序》的一大理论贡献。
其二,是对诗的美刺作用的强调。《诗大序》说风诗是“下以风刺上”、“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颂诗是“美盛德之形容”。对于雅诗,《大序》虽未明言,但通过《小序》可以看出,《诗序》的作者实际上认为风、雅中都有美刺。如《小雅·庭燎》“小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序:“规宣王也”;《祁父》序:“刺宣王也”;《白驹》序:“大夫刺宣王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等等。由于《诗经》中刺诗较多,因此“美刺”说特别启发人们把诗歌作为批判黑暗现实和不良政治的武器,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把诗歌的美刺作用理解得过于僵化,没有注意到诗三百篇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多方面性,从而导致对诗篇主题和内容牵强附会的解释。这个问题在《小序》中尤为突出。比如《周南》中的《桃夭》,本是一首欢快的古代古代婚礼时唱的赞歌。《小序》解作:“后妃之致也。不妬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芣苢》,原是表现一群劳动妇女在快乐地采摘车前子。但《小序》说它是“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召南·小星》本是表现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官吏抱怨自己日夜奔忙的命运。《小序》释曰:“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小雅》中的《隰桑》本是表达一个女子对爱人的深厚感情,但《小序》说这是“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这些解释,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儒家学者出于政教中心观念的臆解妄说,象层层瓦砾,掩盖了《诗经》这部古代优秀文学遗产的真正光辉。
第三,是对诗歌风格的要求。《诗大序》提出诗歌风格的理想标准是“主文而谲谏”。东汉大儒郑玄在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这段文字时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不斥言,也就是不直言。要做到委婉曲折、用打比方的办法来旁敲侧击,就必须采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样,“风雅”与“比兴”这两个概念就联系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风雅比兴”。这个说法的含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有美刺,其中最重要的是刺;二是用比兴,即“主文而谲谏”、“譬喻不斥言”的表现方法。这种理论一方面具有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风格必须温柔委婉,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这就为后世封建文人排斥风格粗犷、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品,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四,是提出“变风变雅”的说法并对其加以说明。《诗大序》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则说得更为具体: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僭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变风”、“变雅”是相对于正风、正雅而言的。所谓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是赞美、歌颂性的作品。变风、变雅就是“衰世之音”、“乱世之音”,是充满了“怨以怒”、“哀以思”情调的作品。《诗大序》和《诗谱序》都认为变风、变雅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这种看法有嫌机械。因为事实上,盛世也有阴暗面,有不肖之人和不肖之事,故而会产生讽刺诗;衰世因为社会动荡,也会有志士仁人力挽狂澜,显示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品德,因此也会产生赞美诗。象被郑玄列为“诗之正经”的《周南》、《召南》,就未必都产生于周初,并且其中也有怨刺的内容。不过从总的倾向看,西周前期和后期至东周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诗歌面貌,确实有所不同。后一时期“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其诗歌总的说来具有“刺怨相寻”的特点。所以正变之分指出了时代政治兴衰与诗歌内容的密切关系,由于政治情况不同而决定诗歌内容的美刺,有其合理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诗大序》作者称太平盛世的赞美诗为“正”,把讽刺、抱怨、抗议乱世衰世的怨诗、哀诗称为“变”,这其中的褒贬态度是很明显的。后世儒家正统学者往往崇“正”抑“变”,贬低排斥抨击统治阶级、表达哀怨之情的作品,不能不说其中有《诗大序》“风雅正变”说的消极影响。此外,《诗三百》中还有不少表现非政治性内容的诗,过于强调政教内容就会导致用单纯政治观点去曲解诗歌,也是不利于对原作的准确阐释的。
Tags:
相关推荐
-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60925996.99 元中标红林总装厂房二期工程
- 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龙里县城区排涝工程勘测
- 北京中和联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标山地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植物表型研究设备采购及伴随服务(重新招标)项目,中标金额 7764000 元
- 霸州市佳理鑫五金制品厂中标新乐市第三中学采购项目
- 河北泽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等为路南区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一期)一标段工程总承包(EPC)(二次)中标候选人
- 河北石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110736.93元中标高铁片区景观提升项目施工三标段
- 中基恒源建设有限公司中标高铁片区(含新华商业广场)景观提升项目施工五标段,中标价 13430852.95 元
- 九芝堂换帅完成工商变更
-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宁县水果供应链基地运营配套建设项目施工(二次)第一中标候选人
- 浙江宁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97028327元中标慈溪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转运一体化建设项目(一期)